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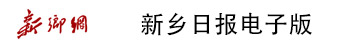


一个称呼背后的空白
□刘天文(辉县市)
“爷爷”对我来说,仅是一个名词,一个卡在喉咙无法喊出的称呼。
爷爷走得早,走得匆忙,没跟我打个招呼,甚至没顾上在我身上轻轻地一瞥。我坚信在我懵懂的幼年,爷爷抱过我,逗过我,亲过我。而父亲给出“你出生前你爷爷就走了”这个残忍、冷冽的事实。爷爷走得干净、干脆,他抛弃了人世,决绝得连一张黑白照片都没留下。无数次,从奶奶、父亲、伯父、姑姑的只言片语中抽取、搜刮淡薄缥缈的讯息,构画爷爷的模样。他总是残缺不全,少胳膊缺腿,任凭我如何努力,他的面目五官还是无法显现。
他就是一个人形空白。
奶奶的晚年,一根拐杖陪着她,即使夜里,拐杖也立于靠近奶奶头部的床侧。我想,支撑奶奶行动的,应该是爷爷的“搀”,而不是奶奶使用拐杖时的那个“拄”。一度恍惚,和奶奶彼此互为影子的拐杖就是爷爷,它会搀扶,它会陪伴,它会倾听。一定是这样。奶奶走时,和她并排睡在棺木中的是那根拐杖。爷爷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,同时也给予我一个残缺破败的童年。
小时候,和玩伴打架,我打赢了,玩伴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喊爷爷去。”我和他都坚信,爷爷身负神通,无所不能,大喊一声会身驾祥云前来,是无往不利的法宝。我打输了,会梗着脖子:“我也有爷爷。”只不过泪珠在眼里打转,我口中的“爷爷”,对应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只是一个人形空白。相对于父母的苛责,爷爷那无论错了时的宽容,闯了祸的包容,无法无天地纵容,我全享受不到。我是多么渴望有个爷爷,哪怕是一个瘸腿的、瞎眼的、乞丐一样的爷爷。“爷爷”这两个字,成了我童年、青年乃至中年提起时的无穷惧怕。“爷爷”这两个字,对我只适合收藏,不能说,不能想,不能忘。
每次身心疲惫,心力交瘁,便会和爷爷来一次私密相会。爷爷不是主动来的,是我把他拘到梦里,对着一个虚无缥缈的人形空白无声倾诉。想必爷爷是不会安慰人的,不然,醒来我怎会泪流满面,然后默念:“爷,爷……”我不喊“爷爷”,似乎两个字拆分了我饱满外溢的情感,远没有一个“爷”字浓缩,更显情深,更显意切,更为刻骨,更适宜在舌尖滚动,更易于心头温养。只是这一个字,我只能在夜里呼喊,在梦中呓语,在心头呢喃。
父亲偶尔长叹:“要是你爷爷活着……”这句话省略的,是我和父亲无限的感慨,无边的惆怅,无穷的念想,无尽的怨恨,还省略了爷爷本该漫长的余生。
一度认为,奶奶即使坐着,也握着拐杖“咚咚”地敲击地面,是发出某种密码,和地下的爷爷交流。我没有爷爷的联系方式,不过终是相信,爷爷不过是一次远途,不过是孩子似的贪恋路上的风景没有返回;终是相信,他在远处等着我,或者是不远处,以微微下蹲的姿势敞开着怀抱,伸展着双臂,慈祥,煦暖,等着我乳燕投林,包裹我的喜怒哀乐,填满含饴弄孙、天伦之乐背后的虚无,缝补我和他此生的断裂……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