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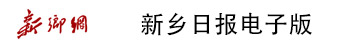


冰是睡着的水
吴芜(原阳县)
我其实不接受律师写诗。试想李白替月亮写辩护词,白居易为卖炭翁讨公道,杜少陵带三吏三别法庭陈诉短叹长吁,任法官敲碎法槌也难震出个庄严来。
邢体兴是律师,写诗。
“冰是睡着的水”,是他诗集里经典的句子。当然,集子里这样经典的句子还有很多。
警惕或者说略带不安地拿到他厚厚的诗稿,我笑了。《法间余墨》,这不说的就是间作套种嘛!豆棵趟里长高粱,谷子地里点花生,不成垅不成行,有意无意似长似留地东一堆西一片散淡开去,人也朦胧,风也迷离。也好,我一脚踏进田地,管他高矮错杂绿肥红瘦,花掉大半天光景,倒也酣畅淋漓地探了个究竟。
邢体兴出生黄河岸边,若诗意地说黄河水奔流血脉,涛声回响于灵魂深处,只能是后话,是长大以后的事情。写诗以前,走出那片滩地之前,他或许没有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。那时候家穷,穷家陋舍搭一棚茅草搁在起伏的沙岗上,画风更是枯寂和无奈。好在他有玩伴。打架,偷瓜,偷苹果,他们尝试了乡间所有快活的恶作剧。
吃不准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,取得律师资格之前还是之后?离开家乡后他做过很多事,去过很多地方,认识很多人,还结识有写诗的朋友。这从作品中都可以看到,偶尔他会与那些写诗的朋友聚在一起,推杯换盏海阔天空放浪形骸。有一回他们还拜谒杜甫墓。
一进院子/都光想哭/除了碑林/就是光秃秃的坟墓
诗圣一辈子贫困/死了也没有个/风光的住处
哀其诗,悲其人,怨其世道。
他结识的所有人中,最重要的是位女孩儿。他们相爱了,真诚而持久,他在诗中反复吟咏,多数都是说给那女孩儿的。有首《桃仁》我喜欢——
她给我一枚桃/羞怯地说/拿着
我知道/这是爱情/心儿一颗
我还她赤裸的核/说打破它吧
我的心就在这里躺着
他们成家了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男人担起家庭重任的同时也揽起更多的社会责任。他很忙,忙到顾不了家,偶尔回到原来的老家成为渐次苍老的概念。河水涨了,河水落了,草木变换季节的颜色。
不知从哪天起,父亲老了,腰板没那么直了,母亲头上白发绺绺,遮都遮不住。记忆的沙堆没了,仿佛被风一夜铲平,沙堆周围的疏林,刺槐,苦楝,不成样子的沙枣被连根儿拔去。杨柳间,新房落成是谁家?再后来,父母相继离去,乡亲在白花花的哭嚎中将他们一一送到村外,滩野茫茫。
心空了。这是人类的共性,长再大失去父母都会绝望和孤独。灵魂开始漂泊,也开始内省。回忆潮水般涌来。草屋,石板,老椿树,昏黄的油灯,风雨的夜晚,母亲的双手,全都具象、生动成时间冲不走的石头。
还没来得及看春天的花/夏天的绿就浓了/还没来得及淋夏天的雨/秋天的黄就到了/还没来得及赏冬天的雪/春天的花就开了/还没来得及听感恩的话/您的耳朵就聋了/还没来得及接受我的报答/您就匆匆走了
好想再听您的唠叨/好想再轻抚您的白发
——《曾经听过的一首歌》
他这样写父亲:
一个黄河边的农民/和累倒的牛/一同走向生命的终点
这是黄河父亲,是中国父亲。
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幅老照片,老牛紧绷套绳,犁铧深插泥土,犁弓着,赤着上身扶犁的农夫腰弓着,整片翻开的土地泥泞着。
看到邢体兴这首诗,我又想到了那幅老照片,那犁,那牛,那人,那天,不就是老照片上的那个样子吗?
邢体兴以诗抒情,以诗记事,以诗发表对时事的看法、对他代理案情的理解。思也诗,诗也思。
当然,就像无法保证金秋开炸的豆粒颗颗饱满珠圆玉润,而难以强求一个人的诗作字字珠玑无可挑剔。他有些诗流于直白、口水化,其观点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,但不妨碍对他诗意生活的赞许。
换个角度,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诗里,活成诗,纯净质朴优雅无虞,世界每天该获多少点赞?
突然有个想去旁听邢体兴代理诉讼的冲动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