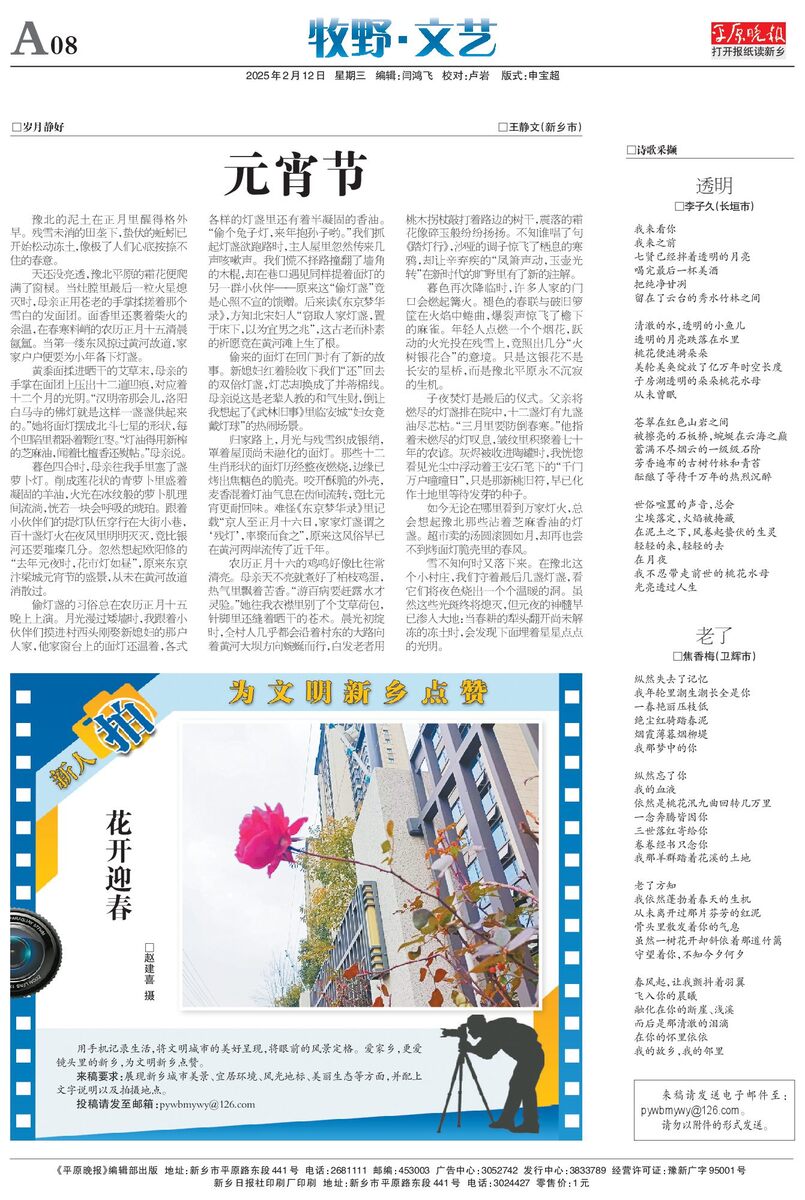元宵节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□王静文(新乡市)
豫北的泥土在正月里醒得格外早。残雪未消的田垄下,蛰伏的蚯蚓已开始松动冻土,像极了人们心底按捺不住的春意。
天还没亮透,豫北平原的霜花便爬满了窗棂。当灶膛里最后一粒火星熄灭时,母亲正用苍老的手掌揉搓着那个雪白的发面团。面香里还裹着柴火的余温,在春寒料峭的农历正月十五清晨氤氲。当第一缕东风掠过黄河故道,家家户户便要为小年备下灯盏。
黄黍面揉进晒干的艾草末,母亲的手掌在面团上压出十二道凹痕,对应着十二个月的光阴。“汉明帝那会儿,洛阳白马寺的佛灯就是这样一盏盏供起来的。”她将面灯摆成北斗七星的形状,每个凹陷里都卧着颗红枣。“灯油得用新榨的芝麻油,闻着比檀香还熨帖。”母亲说。
暮色四合时,母亲往我手里塞了盏萝卜灯。削成莲花状的青萝卜里盛着凝固的羊油,火光在冰纹般的萝卜肌理间流淌,恍若一块会呼吸的琥珀。跟着小伙伴们的提灯队伍穿行在大街小巷,百十盏灯火在夜风里明明灭灭,竟比银河还要璀璨几分。忽然想起欧阳修的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”,原来东京汴梁城元宵节的盛景,从未在黄河故道消散过。
偷灯盏的习俗总在农历正月十五晚上上演。月光漫过矮墙时,我跟着小伙伴们摸进村西头刚娶新媳妇的那户人家,他家窗台上的面灯还温着,各式各样的灯盏里还有着半凝固的香油。“偷个兔子灯,来年抱孙子哟。”我们抓起灯盏欲跑路时,主人屋里忽然传来几声咳嗽声。我们慌不择路撞翻了墙角的木棍,却在巷口遇见同样提着面灯的另一群小伙伴——原来这“偷灯盏”竟是心照不宣的馈赠。后来读《东京梦华录》,方知北宋妇人“窃取人家灯盏,置于床下,以为宜男之兆”,这古老而朴素的祈愿竟在黄河滩上生了根。
偷来的面灯在回门时有了新的故事。新媳妇红着脸收下我们“还”回去的双倍灯盏,灯芯却换成了并蒂棉线。母亲说这是老辈人教的和气生财,倒让我想起了《武林旧事》里临安城“妇女竞戴灯球”的热闹场景。
归家路上,月光与残雪织成银绡,罩着屋顶尚未融化的面灯。那些十二生肖形状的面灯历经整夜燃烧,边缘已烤出焦糖色的脆壳。咬开酥脆的外壳,麦香混着灯油气息在齿间流转,竟比元宵更耐回味。难怪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“京人至正月十六日,家家灯盏谓之‘残灯’,率聚而食之”,原来这风俗早已在黄河两岸流传了近千年。
农历正月十六的鸡鸣好像比往常清亮。母亲天不亮就煮好了柏枝鸡蛋,热气里飘着苦香。“游百病要赶露水才灵验。”她往我衣襟里别了个艾草荷包,针脚里还缝着晒干的苍术。晨光初绽时,全村人几乎都会沿着村东的大路向着黄河大坝方向蜿蜒而行,白发老者用桃木拐杖敲打着路边的树干,震落的霜花像碎玉般纷纷扬扬。不知谁唱了句《踏灯行》,沙哑的调子惊飞了栖息的寒鸦,却让辛弃疾的“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”在新时代的旷野里有了新的注解。
暮色再次降临时,许多人家的门口会燃起篝火。褪色的春联与破旧箩筐在火焰中蜷曲,爆裂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年轻人点燃一个个烟花,跃动的火光投在残雪上,竟照出几分“火树银花合”的意境。只是这银花不是长安的星桥,而是豫北平原永不沉寂的生机。
子夜焚灯是最后的仪式。父亲将燃尽的灯盏排在院中,十二盏灯有九盏油尽芯枯。“三月里要防倒春寒。”他指着未燃尽的灯叹息,皱纹里积聚着七十年的农谚。灰烬被收进陶罐时,我恍惚看见光尘中浮动着王安石笔下的“千门万户曈曈日”,只是那新桃旧符,早已化作土地里等待发芽的种子。
如今无论在哪里看到万家灯火,总会想起豫北那些沾着芝麻香油的灯盏。超市卖的汤圆滚圆如月,却再也尝不到烤面灯脆壳里的春风。
雪不知何时又落下来。在豫北这个小村庄,我们守着最后几盏灯盏,看它们将夜色烧出一个个温暖的洞。虽然这些光斑终将熄灭,但元夜的神髓早已渗入大地:当春耕的犁头翻开尚未解冻的冻土时,会发现下面埋着星星点点的光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