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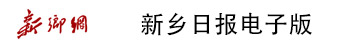


一把肉钩
在富康社区别墅餐厅外的后窗上,悬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挂肉铁钩,那是我特意保留下来的。每当我看到它,就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。
在我14岁那年,父亲因久病去世,抛下了妻子和5个孩子,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。到年底的时候,像我们这样劳力少、人口多的家庭,不但分不到钱,还要欠生产队的债务。
过了腊月二十三,劳力多人口少分到钱的人家,开始兴高采烈地买新布、做新衣,买肉买菜,购置年货。而我家,母亲把分到的棉籽油拿到集市上卖掉,又扯些布给几个妹妹做年衣。邻居陈大娘知道了,就给我们送来半碗猪油。
怎么办?晚上我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贪吃的本能、对新年的渴望促使自己绞尽脑汁、冥思苦想。
常言说,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猛然间想起:前几年父亲身体尚好时,帮人家宰羊的情景。每次有人请父亲帮忙宰羊,都会把羊杂等送给父亲。那时羊肉、羊皮贵,羊头羊蹄不值钱。父亲就将这些带回家,让母亲烧好开水,帮着褪毛、刮皮。只要掌握好水温,羊蹄甲用斧一砸,手一掰就掉了。
那时已进入腊月二十二,一直到大年三十上午,我家附近熙熙攘攘,人们忙着赶集,热闹得很,而我家门口,正是牛羊交易市场。
第二天清早,我找到父亲的好友马全仁叔叔,借了40元钱。早饭后,又找到父亲的朋友张定云大伯,用39元帮我买了两只山羊。因为从六七岁起,我经常跟着父亲放羊、看宰羊,有时还帮忙,所以对宰羊并不陌生。回到家,我学着父亲的屠宰程序,先将羊放倒绑好。再同母亲把案板架搬出来,在下面放一个盆,倒上少许水和盐,以备接血。然后我将羊提到案架上(我10岁起同外祖父习武,也算有把力气),跪紧、放血,松绳、提下来,先在羊后腿靠近蹄部割一小口,用嘴向里面吹气,吹一阵,揉一阵,待羊的整个腹部和四肢鼓起挺直后,开始从腹部下刀剥皮。到腿部时,就需要妹妹们帮忙,用抽筋钩将羊腿拉直,小心翼翼的,不敢将羊皮划破。尤其到了背部,我直接用手按压、扯拽。因为羊皮中间一旦有刀口洞,到公社收购站,就卖不上价钱了。
下一步就需要用肉钩把羊倒挂起来,从羊腹部取出内脏、摘掉苦胆,再剔骨分割。幸亏,父亲逝世后,给我留下了一把大剥刀、一把小剥刀、两把抽筋钩、五挂大肉钩和一杆十六两的老秤。从宰杀到卖肉,所需器具一应俱全。
傍晚时分,在张定云大伯的帮助下,两只山羊肉全部卖出;羊皮晾干后,过了正月十六卖给公社收购站,两项正好卖了40元。而我们全家则过了一个有肉吃的快乐年。
那次宰羊,我第一次尝到了自力更生的甜头,也有了自强、自立的信心和力量。
(老年记者 马安中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