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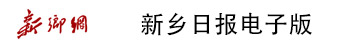


老月饼
|
刘天文(辉县市)
对月饼的记忆,莫过于两个字——甜、硬。
一度认为,先有月饼,后有中秋节,甚至觉得,只要有月饼,中秋节可有可无,完全忽略了月饼与中秋节的依存关系。持有这种观点的,铁定都是吃货,尤其是小吃货,如我。
小时候的月饼,绝对称得上“珍馐佳肴”,属于奢侈品。记忆中,只在奶奶家见到过月饼的真容,都是四个姑姑送的,每人二斤,八个。馅儿都是五仁的,如今居然想不起五仁的种类,只记得里面有花生仁、葵花籽、核桃仁,还对馅儿里纤长匀净的青红丝、晶莹透亮的冰糖记忆犹新。
此后,到来年6月,这漫长的一段时间,32个月饼大多会进入我的肠胃。要不是担心天潮月饼发霉,奶奶能把月饼跨年放到下一个中秋节。这么长时间都有月饼吃,以致到现在我的思维认知,还是偏执如初——月饼与中秋节无关。
月饼的甜,不仅仅是冰糖的缘故,皮,馅儿,从外到里,甜味层层加深,像经过岁月的熏染、沉淀,可以品尝出甜味的层次感和厚重感;且甜得没有道理,没边儿没沿儿,似乎天底下所有的甜,都聚在一块小小的月饼之中。冰糖的功用,是嚼起来“嘎嘣、嘎嘣”那种声觉的享受,似乎就是咀嚼日子,甜,且嘎嘣脆!馅儿里的五仁,包含地里长的、树上结的,每一种都承载了大地馈赠的独特味道。这几样美味混搭在一起,像一家人身居一室,打打闹闹,却还如此团圆、和谐。吃一口,甜的味道、幸福的味道,掩盖、消融了日子的清苦,美好、希望,便悠长起来,触手可及。
月饼的硬,咬显然有点力所不逮,得啃。稍不用力,一口下去,顶多在月饼边缘留几个白牙印,所以对付一个月饼需要“拼命”的劲头。放到来年的月饼更硬,啃也失去效用,常常是奶奶熬粥时,月饼放锅里,得熬呀熬呀熬,煮呀煮呀煮,冬眠般僵硬的月饼才会苏醒松软。听人说,月饼制作最后一道工序是烘烤,这让我想起村东头的砖瓦窑,砖瓦也是经过烘烤才硬邦邦的。我理所当然地认为,月饼的硬,本来如此,
现在的月饼,酥松、软糯,甚至不用牙齿,用舌头就能消灭掉。月饼的馅儿,三鲜的、枣泥的、红豆的、肉类的、蛋黄的、水果的……种类之多,数不胜数。但我却怀疑这类月饼的正宗性,统统把它们划入包子之列。
有次儿子的学校组织了一场亲子活动,手工做月饼。在现场,我才知道,现在月饼的馅儿和皮,都是用食用油拌和的,难怪不是越烤越硬。想来儿时的月饼馅料一定用水拌和,像做砖瓦一样。
在乡下老家,遇到一位蹬三轮叫卖月饼的老人。四个月饼一摞儿,草纸包裹,顶上搁一方红纸,印有嫦娥奔月的简笔画,最后用土黄色的纸绳捆扎。完完全全就是记忆中老月饼的式样!
买回家,儿子当然不吃,我则啃得津津有味。中年之身,不再注重口舌之欲,在吃的追求上,更多是一种情怀,品咂的,是这种食物和曾经的自己在交融纠缠的岁月中互生的点点滴滴、丝丝缕缕……


